两份证书的回归
发布时间:2022-04-14l 来自小红书的线索
3月17日上午,微信上突然收到了来自多位同事朋友的提示,所有的信息全部是来自小红书上的同一条链接:http://xhslink.com/BiDWG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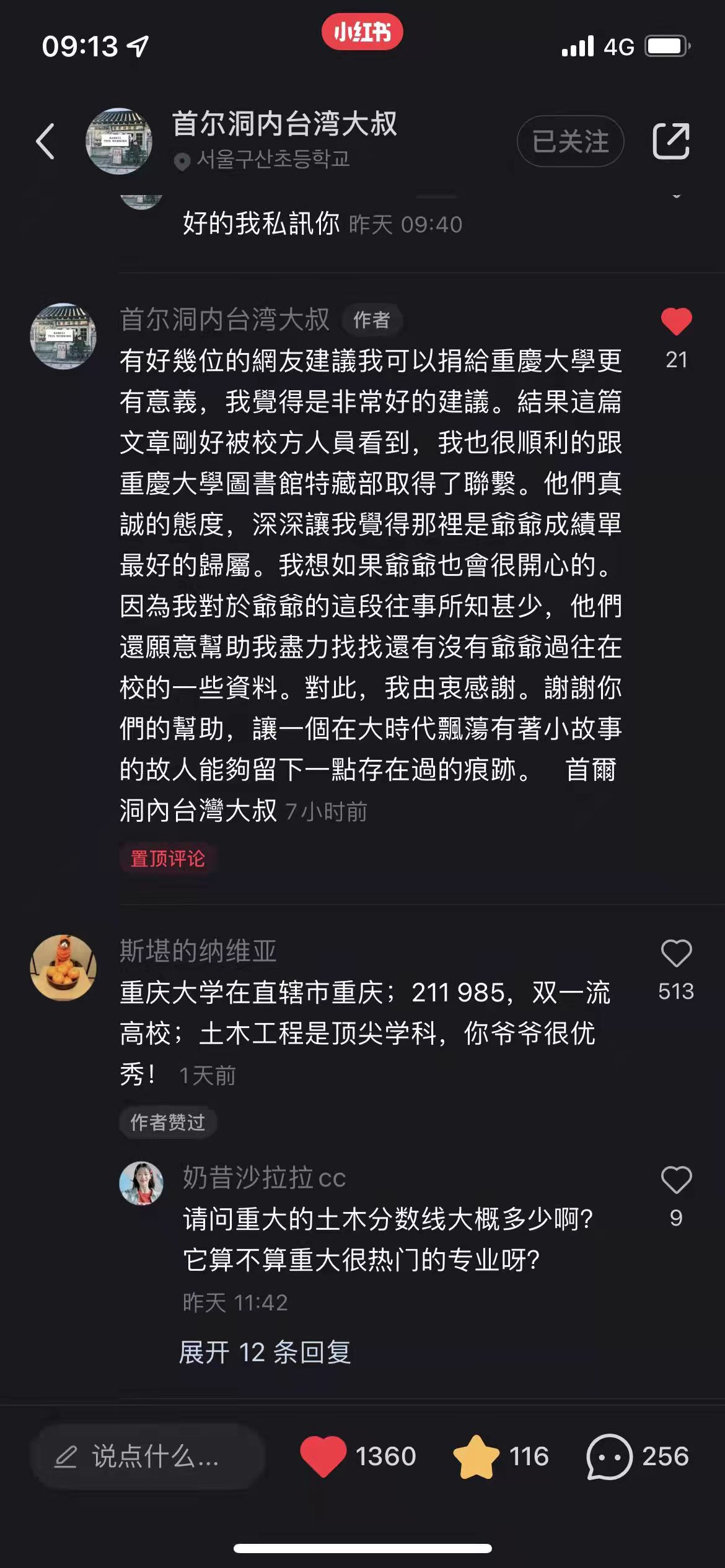
小红书上ID为“首尔洞内台湾大叔”的博主上传了两张图,图中是一份国立重庆大学成绩单封面,另一份是重庆大学转学证明书。配文如下:
“爷爷1942年的成绩单——刚刚脸书的回顾突然跳出来我几年前整理爷爷遗物的照片,看到后突然好思念爷爷奶奶。爷爷在1942年重庆大学的成绩单,看来成绩比我好很多啊之。现在爷爷的遗物我都保存的很好。未来我也会找机会告诉孩子们我们是谁,从哪来。不过对于孩子的未来我不想过多的干预,我相信他们未来会有足够的智慧去决定要去哪!!我们家祖籍江西,对于四川一点都不了解,想问一下有人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重庆大学吗?那是所好的大学吗”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非常棒的收藏品!从事特藏文献工作多年,我们都已经养成“先下手为强”的反射性思维,通过小红书站内信,几个小时后我们便与博主直接联系上。预料之中应该会有一个长长的故事,没有荡气回肠,但因真实而动人。是那个时代里无数平凡人中的一个,见证了历史,也被历史而裹挟。
l 隐匿的足迹
与余先生的交流过程前后持续了一个星期,余先生成长于台湾省,现居韩国首尔,证书的所有人“余毅之”是其祖父。余毅之祖籍江西,1923年生于武汉,12岁离家,后随西迁大流抵达重庆,1944年入重庆大学土木系学习,1946年4月申请转学;或于1948年6月毕业——余先生对于祖父前半生的信息知之寥寥。
从证书上可见,余毅之祖籍江西南昌,1923年出生于武汉,战火肆虐时他选择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哥哥则留在武汉继续生活。为何选择重庆、走的水路还是陆路、随军还是自己走、中途如何躲避战火、何时抵达重庆、落地重庆后如何生活、重庆是目的地还是中转地、为何选择考取重庆大学此类种种均是问号无从解答。
从“国立重庆大学学生成绩簿”和“国立重庆大学转学证明书”上我们可以知晓一些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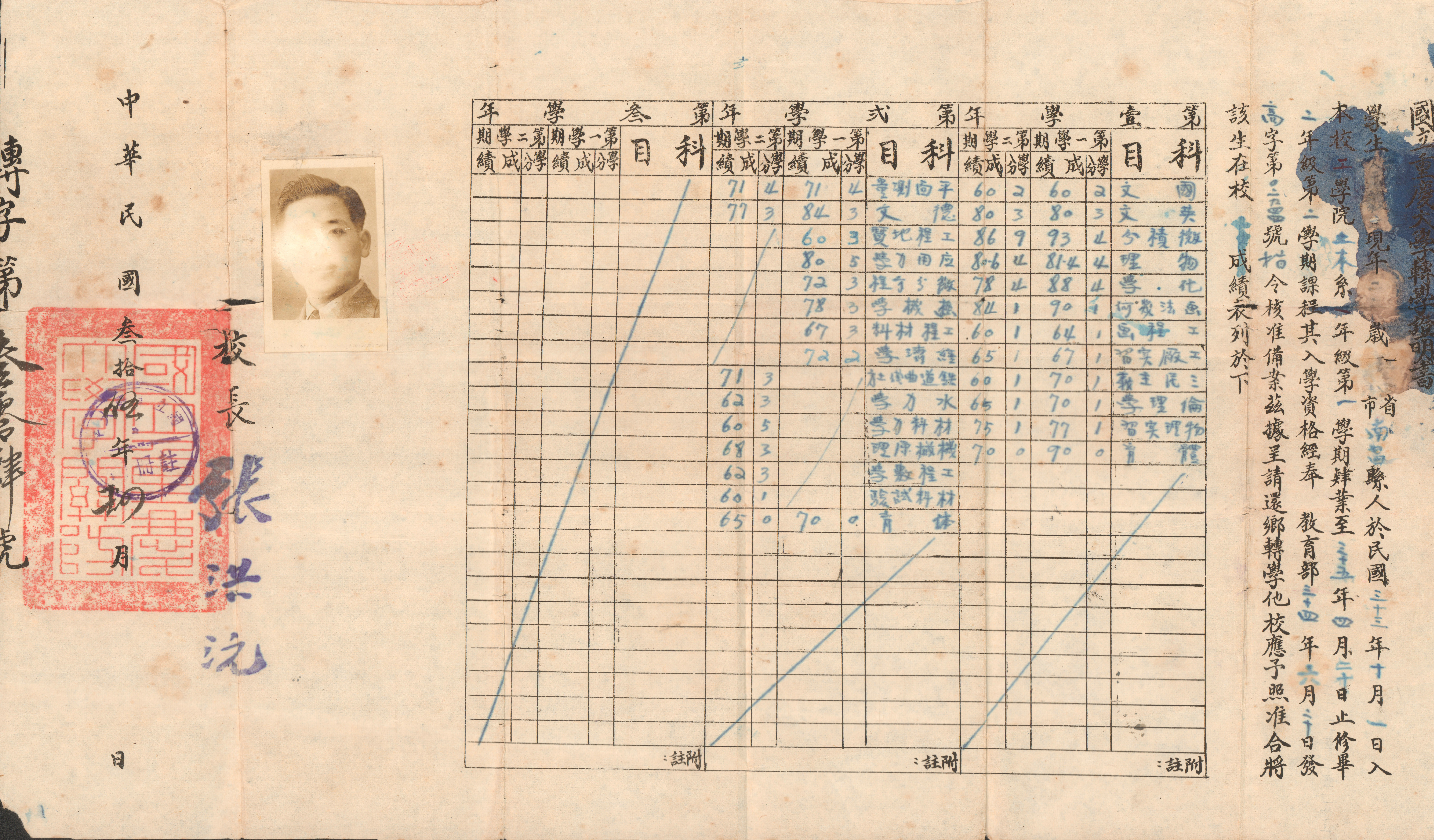
国立重庆大学转学证明书上文字:“学生余毅之 现年二十X岁 江西省/市南昌县人 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一日入本校工学院土木系一年级 第一学期肄业 至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止 修毕二年级第二学期课程 其入学资格奉教育部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发高字第〇二九四四号指令核准备案 兹据呈请还乡转学他校 应予照准 合将该生在校成绩表列于下”
国立重庆大学学生成绩簿上则记录了八个学期的成绩,分别是三十三年度上学期(1944年9月至1945年1月)、三十三年度下学期(1945年2月至1945年6月)、三十四年度上学期(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三十四年度下学期(1946年2月至1946年6月)、三十五年度上学期(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另有三学期成绩尚未标注时间表,推测应该是三十五年度下学期(1947年2月至1947年6月)、三十六年度上学期(1947年9月至1948年1月)、三十六年度下学期(1948年2月至1948年6月)。
从成绩册上看余毅之修业完毕,八个学期的成绩完整清晰,从基础课到专业课再到毕业设计都记录清晰,但转学证明书却是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即1946年4月发放,后面的成绩也没有记录。
综合两份证件判断,余毅之在1946年曾计划随回迁大流返乡继续求学,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未成行,最终选择在重庆大学继续完成学业。
余毅之是什么时候离开重大的?又是什么时候离开重庆的?还乡是返回武汉还是江西?在何处工作并落地生根?何时何因去了台湾省?为何后来不曾告诉亲眷自己在重庆求学的诸多往事?如此种种,困惑重重。而这些困惑也成为我们接下来搜寻的重点,期待从蛛丝马迹中陆续还原尘封的真相。
沟通完毕,余先生发来一段语音:一个人,他曾经在这世界上存在过的一个证明,好好的被保存住,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感谢你们,给爷爷的物品提供一个很好归宿。
l 物回原处
3月30日,余先生将两份证件从韩国首尔寄出;关于“余毅之”的查询我们继续进行。
4月11日,两份珍贵的证件经过了长达半月的旅程,从韩国首尔抵达重庆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办公室。两份证件品相完好,字迹俨然,所载信息历历如初,因浸润足够的时光而格外轻柔泛黄。


1946年从重庆大学第一教学楼发出去的证件,在余毅之老学长的精心呵护下随他辗转半个中国,抵达台湾省,终至韩国首尔,七十二年后的今天再回到重庆大学校园内。第一教学楼依旧,工学院依旧,证件依旧,持有人已然作古,留下了无数谜。在与余先生的多次探讨中,我们推测余先生应该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决定跟随回迁的洪流返回故土,在离开重庆大学时获得这份“转学证明书”,原计划带着转学证明抵达故土后再选择高等院校继续修业直至获得毕业文凭。
但遗憾的是,在档案中查询后暂未查询到余毅之离开重庆大学后的就学、工作资料,具体情形暂时无法确定。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密集的线索,希冀能够查询到余毅之后来的信息,查询到“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里留下的痕迹与故事”。
l 另外一个故事
与小红书上的奇遇不同,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资料收集。
2020年4月至11月,我们陆陆续续从一个二手书店里收回了一千多份资料,记录了一个名叫“邵鹿”的机械系老校友从求学开始到离世之间几十年的故事,求学、肄业、毕业、工作、调动、右派、平反、与老友通信……这足以怀疑是邵鹿去世之后,其保存的资料被打包转移,至于为什么会流入一个旧书店不得而知,最终在重庆大学图书馆永久保存。
邵鹿的成绩册编号是32072,余毅之的成绩册编号是33074,馆藏还有一份叶逢年的成绩册编号35203。至此,我们已经馆藏三册四十年代成绩册原件。


邵鹿的资料里有很多在重庆大学求学的相片,原本是为了寻找相似的成绩册,却回想起一张标注了很多名字的相片,刘子真、薛亲民、陈复民……这些活跃在1949年前后的名字于我们而言非常熟悉。
他们都是普通人,当年是普通的学生,后来是普通的社会人员,记得他们的名字是因为在做《文献中的重庆大学1929-1949》时,这些名字曾在一册原始资料中反复出现。而这些名字所隶属的化工研究所,亦是重庆大学最早设立的三个实验室之一,刘子真助教跟随的教授正是彼时的重庆大学化工系副教授、后来的四川大学医用高分子材料专业奠基人乐以伦教授。
邵鹿老先生估计也想不到百年之后自己的这些物件会回到一个他曾经熟悉的地方,永久留在这里。
l 抢救回来的历史
在与余先生的交流中有一个词语出现的频率很高:一个人存在的痕迹。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求学时是普通的学生,工作后是普通的社会人,平凡人的生活大多如此,代代相传循环罔替。史书所刊凤毛麟角,史书之外才是无数人与事幻化的真实世界。漫长的一生,能留下的就是这些散碎物件、只言片语,芸芸众生,万般相似,何其感慨。
与特藏工作打交道数年,每每收藏整理逝者的资料总会得到其家属的多般感谢,因为如若不是我们参与这个过程,不出意外这些资料的归宿必定是废品收购站。我们在这些原本要被粉碎的资料中仔细发掘,一页手稿、一张相片、一个徽章、一份证件、一盘录像带……记录了逝者生前的故事与行迹,无数故事与行迹汇成了一个大时代的片段,最后还原一段段完整的历史。而对于“一个人”而言,很多年以后也许会从我们的珍藏资料中发现曾经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些事,于万古江河而言,已然足够。
就像这位余毅之老先生,余先生言暮年的某些时分爷爷会喃喃自语,那些语言没有人听懂,我们猜可能是武汉话也可能是江西话甚至还可能是重庆话,故土虽离乡音难改,一个流亡学生的前半生几乎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作为那个大时代中渺小孱弱的小人物,被迫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向前,
对于如今的孩子们而言,“战火硝烟”已经成为一个课本上的历史名词,校园内可供凭吊的遗迹恐怕也只有那一尊痕迹深深的“大轰炸纪念碑”,历史的风尘黯淡了昔时的浓墨重彩,即便我们费尽心思也很难在几十年岁月的字里行间里觅得铅尘墨痕。我们尽力收寻回无数的片段,通过拼凑起这些点滴片段,幻想出七八十年前重庆大学校园内阆苑深深、群儒荟萃的蓬勃影像。


